聯合國在29年前,把每年的5月3日訂為「世界新聞自由日」;諷刺的是,原訂在這一天公布結果的「人權新聞獎」,卻在一周前被主辦方香港外國記者會以「不想誤墮法網」為由緊急煞停,再為香港新聞自由敲響喪鐘。過去一年間,在高壓底下,香港敢言媒體紛紛倒下。有香港新聞工作者失去自由,大批香港記者相繼失業、轉行或移民;也有人選擇到海外重整旗鼓,繼續為香港發聲。這一集,我們先來傾聽幾位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故事。在職業生涯的分叉路上,他們如何作出選擇?
「來了三個月,我現在幫市議會做外判交通督導員,負責抄牌,做了一個月左右。」前《明報》突發組記者梁銘康年初移居英國曼徹斯特後,放下拿了六年多的相機,轉而穿起制服、拿起對講機,成為一名交通督導員,專責向違例泊車者發告票。

當記者成了交通督導員
和過去六年緊張刺激的記者生涯相比,這一份相對輕鬆的工作讓他感受到巨大落差。 「工作不難,薪水不差,但就覺得工作沒甚麼意義,和以前的生活比較是完全沒有意義,連帶覺得人生沒有甚麼目標,到了一個barely holding together的狀態。每天起來都不知道是為了甚麼。」
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梁銘康就一直拿著相機,在新聞前線追趕跑跳,捕捉第一時間的新聞鏡頭,也親身感受到港府如何藉棍棒和武力打壓新聞自由。防毒面罩、頭盔,成為他不可或缺的開工裝備。
到《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生效,他見證港府如何高舉《國安法》和「煽動罪」等法律武器,刀不血刃地把香港一個個敢言媒體「凌遲處死」。在《蘋果日報》關停前的最後一夜,他和大批香港記者在蘋果大樓留守,見證編採人員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他們與大批港人在雨中痛別陪伴這位陪伴了大家26載的「老朋友」,走完最後一哩路。

出走的理由
包括創辦人黎智英在內的七名壹傳媒集團及《蘋果日報》高層相繼被捕,被控以《港區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其後再被加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同年年底,《立場新聞》六名高層及前高層同樣被當局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促使《立場新聞》即日下午宣布停止運作。事隔數日,香港《眾新聞》也宣布停運。
短短半年間,三家香港敢言傳媒相繼倒下,新聞工作者被定義不清的《國安法》和「煽動罪」拘捕扣押,也在其他港媒中產生寒蟬效應,相繼「溫馨提醒」記者下筆時要注意避險。梁銘康發現,自己已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梁銘康:我所知道的是,有報館召集所有負責寫文章的記者,「提醒」他們要「專業持平」。我看不到有任何機會,我們可以用2019年前的新聞自由標準去做這一份工作,最終我都是要轉行。既然這樣,不如趁我未到30歲、有BNO,到一個自由度較大的地方轉行。
放不下的新聞理想
抵達英國後,他馬不停蹄找房子、找工作。當一切安頓下來,他反而不能安心。
梁銘康:就是安頓好以後,我開始進入一個比較抑鬱的狀態,沒想到來這邊後,情緒狀態比在香港時還要差。感覺無法和香港切割,比如早前明愛醫院把疑似確診者放在急症室門口,我就會想該怎麼拍。比如昨天銀行劫案,我又會想如果我去採訪的話,我會怎麼拍,好像還有很多留戀在香港。我會形容是無法抽離,你完全變成一個旁觀者了,但你還會不斷想,如果你在採訪現場,你會怎麼做?
本來已打算移民後轉行,不再做記者,卻發現自己始終放不下新聞理想。梁銘康總想起前上司跟他說過,一個記者在入行五、六年後,才會真正理解自己在做甚麼。然而在這個里程碑到臨之際,他卻被迫離開香港和鍾愛的新聞行業。
在一份無法割捨的記者本能下,他近日以特約記者身份撰寫移英港人故事,亦以在英國重投新聞行業為目標,計劃考取駕騎執照、磨煉英語和攻讀學士學位裝備自己。即使深知路難行,他仍願意一試。
然而對於香港新聞界的未來,他不敢樂觀。
梁銘康:可以預視的是情況會繼續差下去,現在港府都已經在討論基本法23條立法,還有《假新聞法》。可以預視的結果就是香港會像現在中國的新聞傳媒業情況一樣,很多東西不能報導,或者報導後會有後果。當香港情況慢慢比現在更衰落 ,我估計會有更多同行移民。

留下來的人
不過,仍然有很多香港記者堅持留下。
去年12月29日,《立場新聞》在高層被捕、資產被凍結後即日宣布停運。當晚在辦公室關燈的,是記者林彥邦。
林彥邦:有種「要完了」的感覺,雖說是意料之內,但原來當事情真的發生時……當晚我們大家都不願離開,你知道過了那一天,一切都不一樣了。是留戀,但你也知道留戀沒有用,你留戀也留不住。
十幾年記者生涯一夜終結,記者身份也被硬生生奪走,他頓覺生活失去重心。
林彥邦:開初那幾天,會覺得自己十幾年來作為一個職業記者的身份和生活模式被剝奪了。它早已不單純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但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這種生活方式沒有了,它完全消失了,這種感覺很難受。

失去記者的身份固讓他感到生活無法適應,他更無法適應的,是失去《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後,香港社會陷入一片死寂,真正重要的新聞隱沒於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官方消息中。
最震動他的一次,是今年三月香港疫情大規模爆發期間,港府在落馬洲邊境興建「方艙醫院」,並在香港和深圳之間興建了一座「臨時橋」,讓中國工程人員及物資直達香港工地。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動用《緊急法》,豁免工地範圍內的工程人員及物資,不受香港法例規管。
林彥邦:好大件事喎!香港和深圳之間突然多咗一條橋喎!而且有治外法權,不受香港法律規管。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沒有人關心這個新聞?我想了很久,於是就自己寫了。我發現原來只要有人提,有人說,大家會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我就想,其實世界需要這樣的資訊。我希望自己即使能做的不多,也能夠做一點點,提醒大家香港發生了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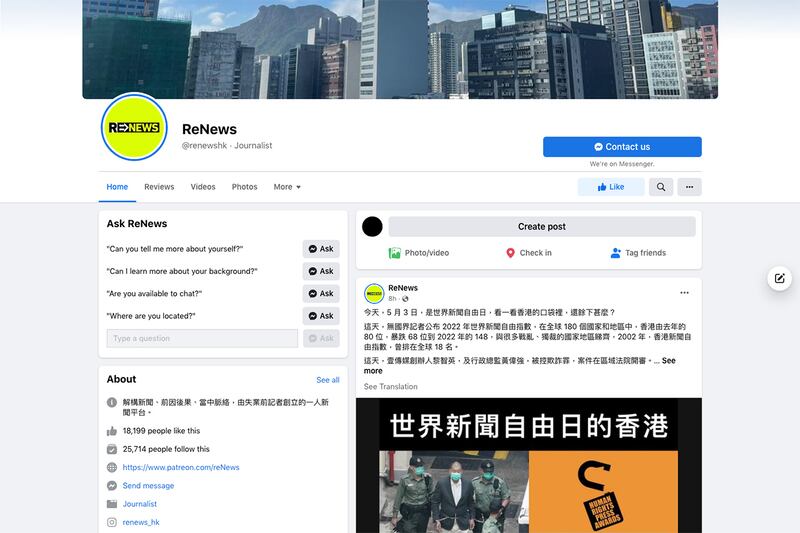
「一人自媒體」 記錄香港「消亡史」
於是,從半個月前開始,林彥邦毅然成立一人自媒體「ReNews」。平台介紹說,這是「解構新聞、前因後果、當中脈絡,由失業前記者創立的一人新聞平台」。林彥邦說,平台取名為「ReNews」,是希望從氾濫的資訊中抽絲剝繭,把重要新聞重新演繹,讓讀者知道如何去理解,同時希望為香港「消亡史」記上一筆。
林彥邦:如果大家經常說「香港死了」、「香港正在死亡」,或者「香港已經死了」,你作為一個在這裡生活的人,你應該要知道她是怎麼死的,過程是怎樣。而不是單單說一句,「冇得救架啦!都唔會有咩改變架啦!」即使你無法改變,起碼你也知道,不要讓她在你眼皮下急劇變壞,而你卻毫無察覺。我不想這樣。
平台推出短短十幾天,臉書上已有超過25000人追踪;內容涵蓋人物專訪、即時新聞、法庭消息,乃至文化評論,所有內容及配圖,都由林彥邦一手包辦。為了讓平台持續運作,他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在接受本台訪問的當下,他同時還在忙著製作日圓貶值新聞的配圖。
平台現時未設付費專區,所有內容免費閱讀,讀者亦可自由選擇付費訂閱支持。林彥邦說,在現時政治環境下,不肯定平台可以營運多久,所以沒有刻意尋找營利模式。現時靠讀者捐款加上自己的積蓄,估計仍可支持一段時間。
雖然經營「一人自媒體」這條路艱難,林彥邦卻並沒有想過要找人一起做。他苦笑說,一是沒有錢請人,二是不想其他人和他一同走這條「不歸路」。一人自媒體,一切責任自負,他反倒覺得輕鬆。
林彥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一個人做,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問責自負。當我不需要顧慮其他人,即使出事了,都是我自己的事,我其實是輕鬆舒服很多。我不用怕自己寫了一篇很危險的文章,結果我上司要坐牢。不用想了,如果出甚麼事,就我自己承擔吧。雖然好像很扭曲,但我覺得我們現在身處一個扭曲的時代,我們唯有用扭曲的方法去思考。
對於政治風險,他表示自己不會「故意撞牆」,不會去寫必然會召致牢獄之災的題材,但他亦不會在政治「紅線」下緣木求魚,刻意尋求絕對的「安全地帶」。他說 「一係就唔做,要做就唔好怕。」
香港記者的抉擇
在大時代下,林彥邦形容,所有香港記者都面對去與留的兩難。而他果斷選擇留下,只是希望能繼續在地感受這座城市的溫度和觸感,並將其傾注筆鋒。他已有心理準備,或要為此承擔後果。
林彥邦:我們面對一個兩難的選項,要不你就留在香港面對那些紅線,一定有些東西不能寫。你總會有恐懼,擔心你寫了某些東西,會帶來某些後果,甚至最終你可能要坐牢。要不你去一個完全自由的地方,擁抱自由的空間,但你就會失去溫度和觸感,你只能夠二擇其一。兩個其實都不好,但你就要選擇。我給自己的選擇就是留下,我想要親身去感受,同一時間我就接受可能會出現的後果。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最新公布的2022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從第80位急跌至第148位,排在菲律賓(147位)和土耳其(149位)中間。無國界記者組織又點名提到《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被強行關閉,造成近 860名新聞工作者失業,部分小型媒體亦因法律風險中止業務。

「他們一下子湧出去,市場完全沒有足夠空缺容納他們,很難得才有部分傳媒願意收留一些人。」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是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 《立場新聞》停運後,他一度短暫失業,其後經同行介紹,加入由前《蘋果日報》記者開設的網上媒體「Channel C HK」。
他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現時工作著重民生議題,和昔日工作內容大有不同,但他理解在香港「新形勢」下,這是必要的轉變。他表示,自己可以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已屬少數幸運兒。其他同行「被失業」後若想重投新聞行業,均面對不同困難。
以《蘋果日報》為例,過去在業內一向以「人工高、福利好」見稱。 《蘋果日報》關閉後,報社資深記者很難在市場上找到能提供相應待遇的新聞工作崗位。相較之下,年輕記者則較有彈性轉投其他新聞機構,但部分年輕記者或習慣自由的工作環境,轉投其他傳媒機構後或有期望落差,大批記者因而轉行,造成轉重流失問題。
以《立場新聞》為例,陳朗昇表示,只有約三分一記者能重操故業,包括以兼職或特約形式繼續報導的記者。 「有些同事開網上服裝店,在網上賣衣服;有些繼續做一些影像或攝影工作,但和新聞無關,有些就去做撰稿員。」
香港記者協會為失業記者提供的支援,包括發布招聘資訊、發放市民捐贈的購物券及失業救濟金。然而不少記者放下筆桿後,選擇靠自己雙手糊口,在餐廳做待應、在麥當勞做收銀員、做的士司機、做公關等。
陳朗昇說,有能力移民的記者,也很難在海外加入當地傳媒,而海外華文媒體亦更傾向於選用中國人或台灣人,使香港記者在海外重拾筆桿的機會少之又少。
當香港本地的新聞空間愈來愈小,有香港記者、傳媒人和評論員就選擇在海外自立門戶,繼續為香港發聲。下一集,我們繼續傾聽香港記者的故事。
記者:呂熙(倫敦) 責編:畢子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