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有关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知名网站《China Heritage》(《遗典》),发表了我就正在全球大流行的瘟疫——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而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以及我与居住美国华盛顿州的译者Ian Boyden的对话。Ian Boyden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诗人,曾在中国和日本学习多年,最近出版诗集《A Forest Of Names》,与2008年汶川地震中殒命的学童有关,而他是以一些孩子的名字为题来探究命运与灾难,并试图让被消失的沉默者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同时让更多的人铭记。几年来,Ian Boyden翻译了我的多首诗歌,这次在翻译120行的《时疫三行诗》时与我作了以下对话,实际上是两个精神流亡者关于各种瘟疫尤其是政治瘟疫的思考,而不只是目前人类正在经历与挣扎的这一种时疫。
伊安:你写的这四十首诗(集合为一首诗)是对因果的深刻沉思,使我们能够洞悉你(作为作家,佛教徒,流亡的藏人,政治异见人士)如何感知和应对这场瘟疫的大流行。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疫情,我觉得自己迷路了,也知道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一首诗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黑暗中看清楚这一点。你能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产生的吗?
唯色:你知道我最初发给你的草稿只有二十八首,那是三月初。随着这个瘟疫的蔓延,趋向内心的思考越来越深入,诗句也因此越来越涌出,而到最后成了现在这样。一开始,肯定不止我一个人,相信谁都会被这看上去像是突如其来的瘟疫给惊吓住。但也是从一开始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事实上,我觉得伴随着这个瘟疫而至的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瘟疫,或者说,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更为可怕的瘟疫,才会出现这场传染病。因果关系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今天,无数的人在困惑这个名叫“武汉肺炎”或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但用佛教的一句话来讲就能明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或者用更简单的一句中国谚语来讲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首诗正是在我这样的认知与感受中,被疫情酝酿着,产生了。
伊安:我刚读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78年写的一篇文章,“疾病是一种政治隐喻”。她写道:“对任何重要的疾病,特别是如果其物理病因尚不明确,并且对于治疗无效,往往充满了含义,……该疾病本身就成为一种隐喻。”比如癌症的异常且不受控制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的异常且不受控制的增长有关;结核病与浪费财富有关,等等。在你这首诗的第一节你写道:“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我不禁认为你把病毒流行当成比喻,指的是一场政治疫情,有这个含义吗?
唯色:其实我的这首长诗不只是对因果的沉思,更是一首批判性质的诗歌。主要是对政治瘟疫的批判,但表达得比较隐晦,这是因为恐惧所致。事实上在这首诗的写作过程中,政治瘟疫的压迫并没有停止,连暂停都没有过,而是一直在进行中。我两三次受到压迫者的警告,我远在好几个不同地方的朋友因为我而被警察警告,这正是极权下的真相与现实。
“更有他疫甚于此疫”是这首诗的关键。这个“他疫”,是的,我指的正是政治瘟疫,包括暴政与暴力机器,以及暴民。暴政正是病毒本身。而“他”其实有多重意思:可以是命运,人类的命运;也影射了独裁者,每一个独裁者。
伊安:许多节在整首诗中,有主词或受词故意的含糊不清。例如,当你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其水涌沸……”,“其”指的是什么?该主题在你的诗歌中可能如何变化?这个“其”是病毒吗?或是地狱?或是人间?
唯色:在经文中,“其”是海。其实这段经文对此有动人的描述。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女子为救赎业力深重的母亲而祈祷:“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复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
这个“其”在诗中也如同令人痛苦和恐怖的海洋,不只是病毒等等,而是我们所置身的当代社会或整个世界的隐喻,随着诗句再现。
伊安:人间地狱当然是一个主题。我想起了你的诗《革命的火》里的这句:“透过熊熊火焰的缝隙,仿佛瞬间的空白”。
唯色:佛经中关于地狱的描述很细致,但人们通常不会认为那就是现实。在我看来,我们正是生活在六道轮回之中,流转于十八层地狱之间,甚至当下即发生。这可并不是比喻。
伊安:回到病毒的多重意义,几个星期前艾未未也区分了天然病毒和精神病毒,在推特上写道:“现在看,中国流行的不是一场致命的瘟疫,而是万劫不复的精神疾病。”
唯色:是的,精神疾病,非常准确的判断。个体的精神疾病、社区的精神疾病、地区的精神疾病,乃至整个社会及国家。但不是才患上,而是源远流长。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他疫”感染,并且不断地加深,乃至成为痼疾,甚至有可能是不治之症。我作为一个藏人,更有很深的感触。我的意思是,正如桑塔格关于艾滋病及其隐喻那篇,其中写道“异域来源与可怕疾病之间的联系”。我当时在阅读时写下这段话:“那么,作为异域之国,带给图伯特的瘟疫又有多少呢?瘟疫伴随着殖民化,所以当SARS在北京流行,拉萨竟也如临大敌。应该做个调查,在图伯特的近代历史上,到底平添了多少过去从未有过的瘟疫?当有人把共产主义比喻成艾滋病时,被殖民化的图伯特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沦为疫区。”
伊安:实际上,我们的思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具传染性的事物。关于权力的思想是最具有感染的力量之一。
唯色:思想伴随着行动,以致于“祸流四海”。就像奥威尔在《1984》里面的揭露:“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这就是瘟疫。
伊安:或者换个方式,我开始看这种病毒就像是一个陌生月亮,照亮了我们社会的结构,无论好坏。它为你照亮了什么?
唯色:如果要把病毒看作是一个陌生的月亮,那我们是不是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因为在我们熟悉的世界,月亮也是熟悉的,那么是不是也就容易被忽视呢?好吧,如果是陌生的月亮,那可能很不同,那在黑夜中特别清晰的月亮散发着清冷的月光,可以照亮生命本身,也就会真切地看见生命的无常。这倒是一件好事。与此同时,我的佛教信仰让我知道生命并不是这一世的,而是累世的,认识到这一点,会让人多少有些释怀,而不至于陷入焦虑和恐惧。
伊安:但这不仅照亮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我认为该病毒可能是一种革命力量。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因果关系的沉思:“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们可以改变病毒的因果关系,使其最终让人道受益吗?
唯色:你说得太契合我的本意了。是的,与此同时,那清冷的月光也照亮了一种更深刻的关系,我认为是因果律,即业力。正如我最近读到近四百年前的五世尊者达赖喇嘛的一首诗歌,其中这句击中了我:“那些因业力而觉醒的人会跳舞”!我仿佛看见,在遭受各种瘟疫的众生当中,只有因此而觉醒的人,才会跳起生命的舞蹈,那是非常美好的舞蹈。
不过是否可以改变病毒的因果关系,从而受益于人道?我觉得这与每个人自己有关,或者说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只有人人因为畏果而去行善积德,这个世界的灾难才会少。
伊安:在第一章的第3节中,你提及野草,我当然想到了惠特曼的《草叶》,其中每片草叶都是个人的象征,草地是人类社会本身,草是象征民主。但你忽然话头一转,说它像韭菜。你能否详细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唯色: 不,我想到的野草跟民主没有关系。我也没有想到惠特曼。无论野草还是韭菜,在我看来都是弱者,最弱的生命,被那把大镰刀割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大镰刀就悬在每根野草或韭菜的头顶,会随时疯狂地割啊割。
“韭菜”是中国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因为韭菜可以反复收割的特性,所以泛指所有被反复压榨却无力逃脱的弱者。而被反复压榨的过程被形象地描述为“割韭菜”,那获利的一方则被比喻为镰刀。这个说法最初源于金融或经济圈,但现在已经被相当多的人用来形容自己和他人。我们当然也知道那镰刀比喻的是谁。
伊安:这场瘟疫开始后,我决定重读加缪。我发现这种观察特别有意义:“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对人道的尊重的问题。这个想法会让人笑,抵抗瘟疫的唯一手段是对人道的尊重。”你对这个观察有什么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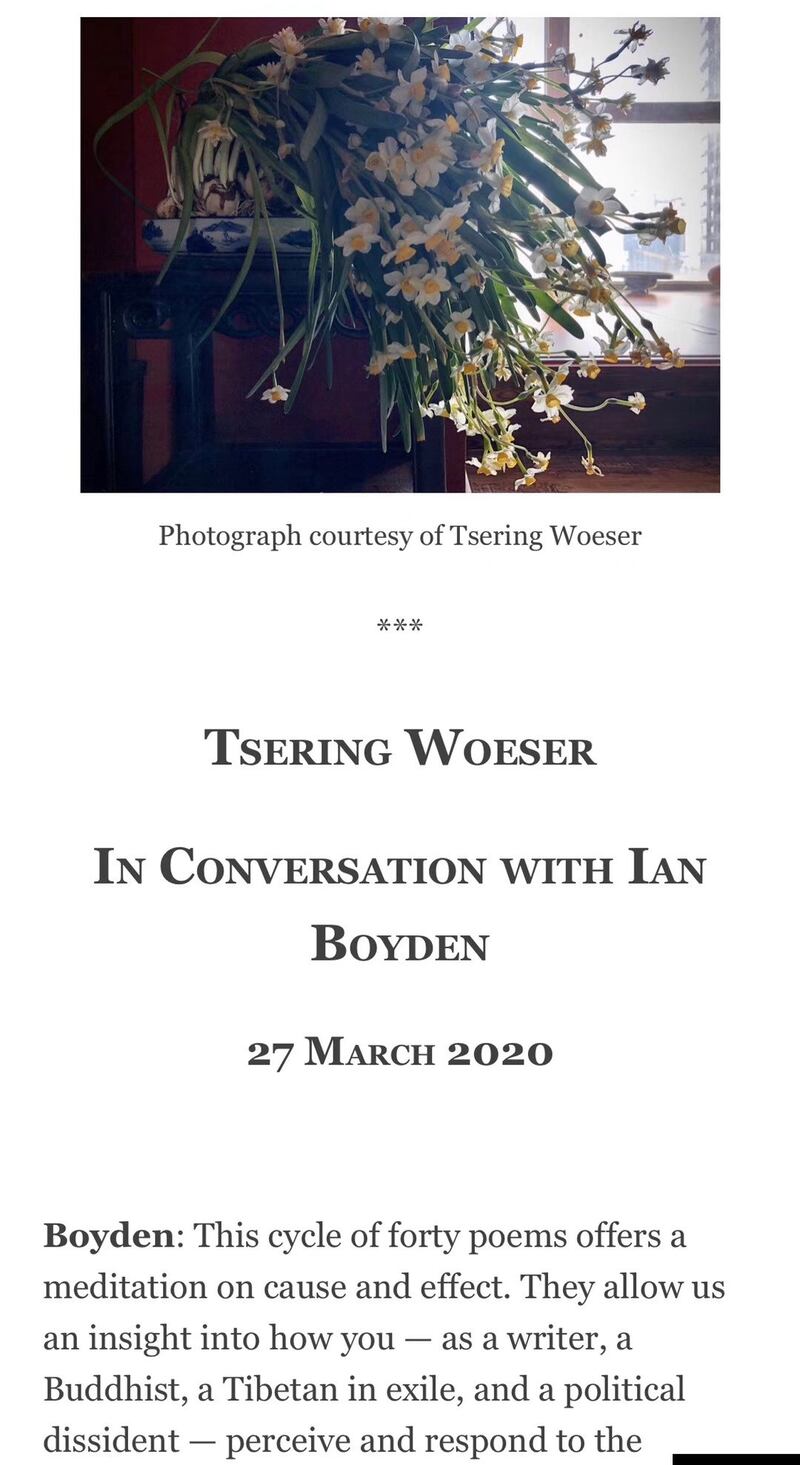
唯色:这个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现在遍及全球,不同的政治制度即极权社会与民主社会、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不同的地理与气候等等,会表现出各种不同。这是通过比较而产生的不同,然而最根本的不同正是这个:是否对人道的尊重。这一点太明显了,可谓有目共睹。
因为没有对人道的尊重,才会造成这场瘟疫的蔓延。我们也只有寄望于对人道的尊重,才可能遏制住这场瘟疫。不然怎么办呢?这个瘟疫显然已经造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伊安:在我们这里,刚刚进入了官方隔离的第一个星期。没有飞机,几乎没有汽车,好安静。我觉得自然界正在呼吸。同时,有一种可怕的黑暗和某种预感:最黑暗的时刻还没到来。那么你在北京感觉如何?
唯色:我在经历了两个月的隔离之后,事实上,那种末日感并没有消除,虽然现在北京看上去似乎取得了抗击瘟疫的胜利。此刻已经是深夜,可是窗外楼下的大路上,车辆驶来驶去,发出很大的声音,就像是因为瘟疫而死气沉沉的这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消失了,甚至可以被忘却了,而人们又在为挣钱忙忙碌碌。
伊安:实际上,今晚我感到很孤独。我不想告诉我的朋友,我已经以自我隔离的方式生活了十年多了,这与瘟疫的隔离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不是作为隐士,而是一个试图了解自我的人……又复杂,又简单。有着一颗流亡之心的译者。你呢?你怎么会这样敏感化地过生活?
唯色:自我隔离的方式!事实上前几天,艾未未跟我和王力雄也讨论过这个。我的意思是说目前的这种因为疫情而隔离的生活,对于我们其实并不陌生,也不存在难以适应的问题,因为我们早就被隔离多年了!在政治瘟疫的威胁下,我们作为写作者却因坚持真实的写作,争取言论自由的表达,而丧失人身自由的诸多权利。被当做某种病毒而与社会、与他人隔离的生活,在我已成了我的生活本身。或者说,多年来,我一直过着一种内心流亡的生活,所以我不太觉得目前的隔离会有多么难熬。
伊安:你要写这首诗给谁?这首诗的观众是谁?
唯色:我写这首诗是为这个时刻:瘟疫时刻。这个不亚于世界大战的瘟疫,不亚于侵略、屠戮、占领、殖民的瘟疫。作为一个经历者、一个见证者,如果不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辜负。而我这次的记录方式是写下这首120行的诗歌。不算长,但也不短,辛苦译者了!
伊安:我们谈谈最后一节。首先,我想谈谈中国译者高海阳翻译的种田山头火的俳句。我试着寻找种田山头火的俳句的英文翻译,但找不到。不过这也很好,因为我找到了原始日语版本。我发现我的解释与高的解释大不相同。他的翻译中,诗人正在大声祈祷,但原文却说:“声音浮上著在风中:南无观世音菩萨。”种田山头火没有指出是谁的声音。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声音。但也可能是其他人的,也可能是读者的。声音随风而来。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佛教生态,伴随着祈祷的风。
唯色:我是恰好在疫情期间,读到日本诗人种田山头火的俳句的。你知道他是一位托钵行脚僧人,也就是云游僧,他的俳句中对佛法的感受很深,而他的语言是很美的。我甚至读出了他与诸佛菩萨一起行走的感觉。在路上走着。在风中走着。边走边聊,祈祷就像聊天一样日常。我喜欢风的感觉,我觉得那风是从积雪的珠穆朗玛吹来的,那是真正的纯粹的风,带着我的图伯特故乡的味道,当我在珠穆朗玛的风中放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会感到安慰和不那么恐惧,包括对政治瘟疫的不那么恐惧。
是的,我更喜欢日语版的那种感觉,声音漂浮在风中,声音附著在风中,声音烙印在风中。而这个声音是祈祷,日语的祈祷,汉语的祈祷,藏语的祈祷,英语的祈祷等等。以传统祷词的“三皈依”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来念出,即:皈依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知道,汉语的“南无”正是皈依的意思。
伊安:我们已经把这首诗说成是政治批判了,把病毒当作比喻了,但这首诗也是祈祷。在整首诗中,你引用了许多佛教本文 (佛经,心咒,僧人传记,僧人的诗歌),但最终是你自己的祈祷。在诗的最后一行中,你邀请中阴里漂泊的灵魂再生。在密宗里,中阴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我觉得也可能是这首诗的隐喻,你是否能谈谈?
唯色:中阴的意思很深。佛法对中阴的说明有六种,而不单单只是指人死后的一种状态。我甚至认为,我们——全世界面临瘟疫的袭击而挣扎的人——正处于一种中阴之中,而我们需要走出这种中阴。同时,我把死于这场瘟疫中的成千上万的亡灵称为“徘徊者”,是因为这些亡灵都是突然被瘟疫夺走生命的人,并不愿意死亡,肯定留恋人间的一切,所以在中阴这个灰蒙蒙的空间里徘徊,非常地可怜而不幸。我因此写下这最后的一行,是想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帮助这些突然殒命的人。我是以一个佛教徒的方式,在这首诗的最后为亡灵祈祷、回向。而我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我能做到的,也仅仅是这样了。
2020年3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