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开端:丘吉尔的铁幕演讲,抑或奥威尔的动物庄园?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母校密苏里州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砥柱〉的反共、反苏联的演说。在这场世纪演讲中,丘吉尔讲出了“铁幕”(Iron Curtain)一词,将共产党国家定调为独裁、侵略的邪恶世界,更为往后长达四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拉开了序幕。
丘吉尔在这篇演说中明确指出:“从波罗的海的思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他强烈主张,英、美应结成同盟,制止苏联的扩张。这场演说两个星期后,对抗苏联“铁幕国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
丘吉尔演说后不到十天,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发表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谈话,谴责丘吉尔是“希特勒的翻版”。一九五五年五月,苏联及其仆从国组成华沙公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抗衡。
此种冷战对抗局面,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才告结束,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的终结”——但是,中共取苏联而代之,历史并未终结。
因为“铁幕演说”,一般人都将丘吉尔视为冷战的鼻祖。然而,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被誉为“冷战研究的学科主任”的约翰•加蒂斯(John Lewis Gaddis)则认为,冷战的开端另有其人、另有其事。约翰•加蒂斯在其经典的《冷战》一书中,以非冷战之地理中心的、位于苏格兰西海岸之外海的、几乎与世隔绝的朱拉岛(Jura)所发生的事件为冷战之序幕。
这个岛屿平淡无奇,丝毫不具战略地位,也没有卷入战争之中,为何约翰•加蒂斯偏偏瞩目于此?这个岛屿本身的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地位固然不重要,但此时岛上住了一名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外来者。这位客人也不是政客、将军或富豪,而是一贫如洗的文人。这是一九四六年,身心俱疲的英国人埃里克•布莱尔来此养病——其实,这个海风肆虐的岛屿完全不适合疗养,与其说他来此养病,不如说来此安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布莱尔的妻子在一场失败的手术中意外过世之后,他便选择独居在这个几乎没有修好的道路的小岛上,贫病交加、霜刀雪剑之中,他开始咳血,死神即将来临。
埃里克·布莱尔是一位尚未得到广泛承认的作家,他正与病魔赛跑,竭尽全力修订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他的笔名是乔治•奥威尔,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名为《一九八四》。这部书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阴郁的预测——“如果你想要一个未来的画面,请想象一只皮靴践踏在一张人脸上——永远。”奥威尔的预测如此准确——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中共秘密警察的皮靴就那样践踏在我的脸上,我对中共极权主义政权的体验完全是奥威尔式的。
“冷战”(Cold War)一词确实是奥威尔帮助命名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奥威尔在一篇书评中首次使用「冷战」一词;二战结束两个月后,他再次使用这个词;一九四六年,他又第三次使用。奥威尔在一九四五年的文章《你和原子弹》中写道,冷战是一种“不和平的和平”——这是极具历史洞察力的描述。他的两部小说,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动物庄园》和悲观预言未来的《一九八四》,使他的名字成为广泛使用的形容词。“奥威尔国家”成了封闭的控制制度的同义词。奥威尔堪称“冷战”这个词汇之父,与国际政治观念意义上的“冷战之父”、美国的战略学家乔治·肯楠并肩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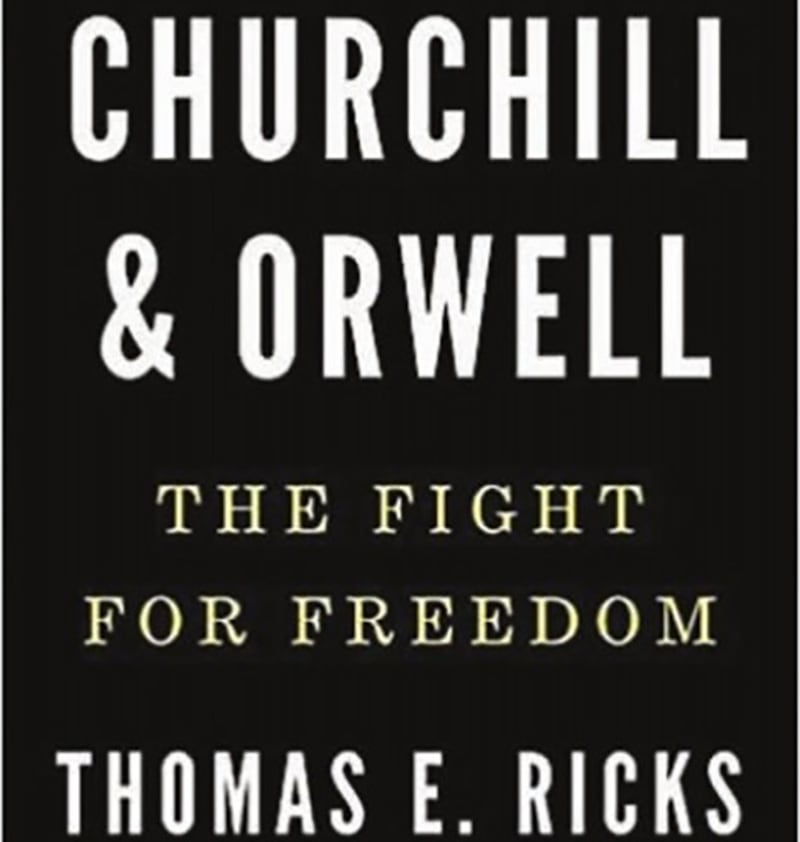
他们如此截然不同,却又如此惊人相似
当然,丘吉尔与奥威尔这两位英国人不会争夺“冷战”这个词语的命名权,他们几乎同步看到纳粹灭亡之后另一种极权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他们的一生中先后奋力抵抗纳粹和共产主义两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美国作家托马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将丘吉尔和奥威尔合在一起作传,使得生前未曾谋面、彼此互不了解的两人神奇地产生了互补与对照,共同构成一部二十世纪人类寻求自由的精彩历史。勇士的勇气迭加起来,可以填海,可以移山,可以惊天地,可以泣鬼神。《丘吉尔与奥威尔》一书,比任何一本丘吉尔与奥威尔的单一的传记都更扣人心弦。
表面上看,丘吉尔和奥威尔的人生是如此不同: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就狂热地嗜好政治,出将入相,最荣耀的成就是在纳粹横扫大半个欧洲之际领导英国对抗纳粹德国,拯救英国于水火之中,他的一生也尽享荣华富贵,美酒、雪茄与美女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反之,奥威尔出生于远东缅甸的一个普通英国殖民者家庭,虽然上过显贵云集的伊顿公学,却从未培养起所谓的“贵族气质”,他唯一担任过的政府公职是缅甸英国殖民政府的基层警察,从未掌握过炙手可热的权力,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试图以笔和纸为谋生手段,生前却不受世人承认,颠沛困顿乃至贫困潦倒而死。
但是,在本质上,丘吉尔和奥威尔这两个人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及“同温层”,逆时代潮流而上;他们兼有战士和先知的双重身份,像远航巨轮的高塔上的瞭望者一样,一旦发现前方有危险事物,明知会遭遇多数人的嘲笑与攻击,却毫不退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向沉睡的本国同胞和整个人类发出掷地有声的警告。
当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颠覆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之后,英国有一部份贵族、政客和知识分子对生机勃勃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了一种狭隘但强烈的认同倾向,甚至对希特勒也五体投地。一九三六年,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拜会希特勒,之后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这位德国领导人“真心希望和平”,英国应当将其当着值得信赖的朋友看待。历史学者本来能够“从历史中看到未来”,汤恩比却被希特勒玩弄于鼓掌之中。
多年后,日裔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在其代表作《长日将尽》中,惟妙惟肖地重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英国贵族阶层虚伪浮华、纸醉金迷的时代氛围,以及他们对纳粹一厢情愿的幻想。一九三六年,英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达顿勋爵组织盛大的派对,一手安排纳粹德国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到其府邸会面和密谈,甚至想进一步促成英王亲访纳粹德国,与希特勒面对面会谈。这位表面上显得文雅高贵睿智的英国贵族和政客,为自己的“和平主义”理想而洋洋得意。然而,达顿勋爵的作为即便不是有心卖国,也是造成了“害国”之恶果。石黑一雄写道:“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爵爷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英国为他摇旗呐喊,助他实施其宣传诡计最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这本小说比历史著作更深刻地刻画出当时英国社会的愚蠢和虚伪。丘吉尔和奥威尔这样的人当然会遭到冷遇和排斥。
如圣经所说,“先知在故乡是不受欢迎的”,丘吉尔和奥威尔是最早识破希特勒真面目的英国人,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丘吉尔因为强烈反对纳粹政权,被奉行绥靖主义外交政策的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长期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同时遭到英国舆论和学术界的耻笑。对此,奥威尔曾指出:“英国统治阶级究竟是邪恶、还是愚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难回答的问题。”
反对共产极权主义是更伟大和更艰难的事业
在希特勒尚未露出狰狞面目之际,反对纳粹德国需要力排众议;而在苏俄异见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尚未出版和中国的文革惨剧尚未传到西方之际,反对共产极权主义是千夫所指的“政治不正确”。丘吉尔与奥威尔一生“反左”,名满天下,亦诽满天下。
经过自己人杀自己人比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叛军杀共和军还要血腥的西班牙内战之后,奥威尔对左派的幻想彻底破灭,转而以批判共产集团和乌托邦思想为志业。即便自己的作品在出版的过程中屡屡受阻(破坏其出版的居然是英国的情报部门),他也毫不畏惧地讽刺那些为独裁者辩护的左派文士说:“他们一嗅到“进步”的味道就立刻蜂拥而来,彷佛苍蝇闻见死猫一般。”如果何谓“进步”必须由某一群人士作出唯一的定义,那么独裁和暴政就近在咫尺。
丘吉尔反共,只是受到左派的恶毒咒骂;奥威尔反共,则面对苏联及其傀儡政党实实在在的死亡威胁。《动物农庄》上市不久后,奥威尔从朋友那里买了一支手枪,说他怕共产党想杀他。两位奥威尔专家约翰·罗登(John Rodden)和约翰·罗西(John Rossi)写道,奥威尔的恐惧可能比他知道的程度还要真实——冷战结束后,曝光的苏联秘密档案显示,当初奥威尔要是被捕获的话,他必死无疑,他确实列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处决名单上。
西方左派文人对异见者的围剿铺天盖地且数十年不停息。丘吉尔和奥威尔共同的论敌、英国左派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从此成为苏联的辩护士,任何对苏联有所不敬的人物,都受到他的攻击。而十四岁就加入英国共产党的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根本不愿翻开丘吉尔、奥威尔以及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霍氏晚年接受加拿大作家伊格纳提艾夫(Michael Ignatieff)和英国BBC电台访问时,都被问到斯大林在苏联推行共产主义,造成将近二千万无辜人民的死亡,是否值得?他的答复是:“如果能创造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值得,也是正当的(justified)”。一九八九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开始崩溃后,霍氏居然痛心到说那是“整个人类的失败”(the defeat of humanity)。这种说法,不是“离邪恶有多远”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构成了邪恶的一部分。
然而,晚近一百年来,丘吉尔、奥威尔、索尔仁尼琴、奈保尔(V.S.Naipaul)等“右派”并不代表西方知识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萧伯纳、沙特(Jean-Paul Sartre)、霍布斯邦、杭士基(Avram Noam Chomsky)等“左派”才是“西方不败”——他们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声称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三十年后的今天,还有那么多西方的“拥抱熊猫派”为共产党中国涂脂抹粉、溜须拍马——他们甚至不知羞耻地炮制出一封“百人联署信”,劝说特朗普政府“不要将中国当做敌人”,声称“此举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究竟是自以为聪明地与虎谋皮,还是愚不可及地引狼入室?中国对西方的文明和秩序已构成严重威胁,危险程度超过昔日的纳粹德国和苏俄。日前,微软新闻发表的一份民调显示,关于“哪个国家对美国威胁更大?”这个问题,北韩得票百分之十,伊朗得票百分之十五,俄罗斯得票百分之三十一,中国得票百分之三十八,中国首次超过俄罗斯名列第一。而且,中国与俄罗斯越走越近,联手反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的态势越来越清楚。所以,虽然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的苏俄都已灰飞烟灭,但丘吉尔和奥威尔的逆耳忠言并不过时——“如自由真有什么意义,那应该就是指把人们不想听的说给他们听。”
有些人只反法西斯主义而不反共产主义,有些人则只反共产主义而不反法西斯主义。丘吉尔和奥威尔的一生跃过了两道深渊,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恶魔正面对决。
用“美好的英语”捍卫自由
相对于丘吉尔生前即享有“立功、立言、立德”的成功人生,奥威尔的名声大都是在身后获得的。奥威尔死后七十年,他工作过的BBC才同意让这位昔日名不见经传的雇员的塑像坐落在公司大厅。BBC时政节目主持人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指出:“奥威尔对真理的信念直截了当、坚不可摧、令人胆颤。他始终在自我批评,也始终在要求读者认真辨别真伪。在假新闻盛行的时代,现在真令人油然而升奥威尔时代之感。我认为他在敦促我们更勤力地去揭示,同时对批评持更开放的态度。”可惜的是,BBC的中文网是中国大外宣战略的重灾区,上面充满了用奥威尔最为厌恶的“新语”写成的谄媚中国的报道,几乎沦为中共宣传部的“英国分部”,奥威尔若看到此种情形,该怎样痛心疾首?
奥威尔不像丘吉尔那样长寿,更没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实现了其理想:“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这两本“小长篇”,可以骄傲地与索尔仁尼琴比砖头还要厚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也使奥威尔得以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的行列。奥威尔对苏俄的批判达到了普世性的高度,比如,以下这段简洁的文字一语道尽了奥威尔那个时代的简史,也是奥威尔展现过人文笔的巅峰之作:
轰炸不设防的村庄,把居民赶到荒郊野外,以机关枪扫射牛羊,用燃烧弹焚毁田舍:这就是所谓的“平定”。无数农民的家园遭到劫掠,他们被迫带着随身行李长途跋涉: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迁移”或“边境整顿”。人民无故入狱多年,或从后脑杓将他们枪决,或是把他们送到北极的劳改营,让他们染上坏血病而过世,这就是所谓的“消除不可靠的因素” 。
这段话不仅适用于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也适用于金氏家族的北韩、波布(Pol Pot)的红色高棉、查维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委内瑞拉、卡斯特罗(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的古巴以及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中国——用暴力和谎言维持的独裁国家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尤其是今天的中国,用“再教育营”来掩饰“集中营”,用“自主知识产权”来掩饰“肆无忌惮的偷窃”,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掩饰“只此一家的天下朝贡体系”。中国这个拥有超过四亿个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和步态识别系统举世无双的国度,比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更像天罗地网的世界——更加恐怖的是,生活在其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由。
丘吉尔和奥威尔不仅批判极权主义,更捍卫“英语民族”的自由传统和英语本身的纯净与清晰。丘吉尔将说英语的人当着同一个民族或同一国家的同胞,并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多卷本《英语民族史》,连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丘吉尔成为极少数以非虚构写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只写到一九零零年,意犹未尽。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为之写了续集《一九零零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他在此书中指出,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有普世价值;相比其他模式,这种模式更适合现代世界。英美两个英语国家相继主导世界进程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这种局势至今仍没有改变之迹象。二十世纪的英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及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反恐战争等四次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四场战争又是“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等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动力。
而今日以英美为核心的自由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文明冲突”,则是其正在经历的第五场挑战与考验。这不仅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工业实力、文化和科技实力的决战,更是要自由、还是要奴役的思想与精神的抉择。在这场战斗中,丘吉尔和奥威尔的遗产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