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常以"56789"几个数字来概括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其中5是指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50%的税收,9是指贡献了新增就业的90%。但近几年,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采取打压和漠视的政策,使民营企业的信心大受打击。去年底中国结束疫情封控、走入经济复苏的通道后,民企的信心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甚至拖累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表现。本台记者王允采写了三集系列报道,以多位民营企业家的经历来揭示中国民营经济遭遇的困境。在以下第二集的报道中,将主要讲述三位服务、贸易类小微企业主的近况。
去年4、5月份上海疫情封控的时候,张开宇想过要和自己的两只猫一起死。
这两只猫他已经养了10年,他说猫就是自己的软肋。不少人的宠物被封控人员消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张开宇尤感恐惧,“我不能忍受他们被锤死,或者我亲手去掐死他们,这太惨,所以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然后把煤气打开,他们就会慢慢窒息死掉,那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这是张开宇能想到的最完美的方案,但或许是因为还有妹妹和母亲,或许是对自由还留有一些向往,张开宇最终没有下手。但这个时候,他心里已经把自己的生意放下了。
离散与溃败
张开宇在上海经营一家时尚精品店,到2022年时已经有十六年的时间。他的客户是上海的富人阶层,在他固定联系的一千名客户名单上,很多人都是身家几千万以上。但上海四月份封控之后,这批客户逐渐离散,“特别是那两个月里,跟朋友聊起来,都是想离开,不顾一切想离开,包括客户和朋友,特别是客户,那些有能力离开的,有钱的,都是这样。”
张开宇一开始还想着维持一段时间看看,但他发现即使留下来的客人消费行为也发生了改变,“就是有新东西上市,你看他们到底来不来,他们有的就不来,或者来了,你看他们,可能看半天就只挑了一件、两件,甚至还是比较便宜的,而且要很长的思考,不像以前就像无脑买一样。”
张开宇很快想通了一个道理,“你看封城这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像被关在一个大监狱里,没有任何自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其实生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到了年底,张开宇就把生意转了出去。
也是2022年,身在成都的莫先生(出于安全考虑,使用了化名)在5月份关掉了在青羊区的最后一家快餐店,并决定永久离开餐饮业。
莫先生2014年投身餐饮业,最好的时候在成都拥有六家餐馆,但到2022年时已经只剩下两家快餐店。他最后关掉的这家快餐店仍然是赚钱的,但他最后还是决定不做了,“当时就是不明朗嘛,2022年的5月份疫情还没有结束,还在陆续的封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封到成都了;一封的话就是两三个月,又要做不起来了,你的库存、你的人工、你的房租还是要付,虽然说还可以盈利,可以赚一部分钱,但一停工,这些钱都已经投进去的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而杭州的葛平创办的咨询公司好不容易熬过了2022年严酷的封城,还是选择在2023年初为其旗下的子公司办理了“歇业”。为安全起见,“葛平”以化名接受采访。
根据2022年3月开始实施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所谓歇业,是指企业如果遇到天灾、疫情等不可抗力的情况,可以申请保留主体资格,不按停业处理,待情况好转后重新启动。但葛平并没有觉得所谓“歇业”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好处,“后面发现,歇业的企业这些基本的支出,财务的费用,税务的费用,租写字楼、租工作室的费用都是要出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保主体,就是不让市场主体退出得太多,政府是有这个考虑。”
葛平揣测,政府推行这个“歇业”制度就是为了在报表上好看一些,不让停业或注销的企业显得太多。
爱自由
上海的张开宇、成都的莫先生名下企业的关闭,以及杭州葛平的子公司歇业与同一时期中国成千上万民营中小企业在困境中挣扎、直至关闭的境遇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据港媒“香港01”去年底报道,企业征信网站“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2年截至11月底,中国有190万家零售业企业关闭,同时有49.6万家的餐饮相关企业注销登记。而这些类型的企业都是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
但张开宇和莫先生这样的服务、贸易类中小微企业遇到困境并不单是因为疫情及封控措施,早在疫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嗅到了经济不妙的苗头。
张开宇的店开在上海法租界的黄金地段,周围街区都是粗大的梧桐树,用他的话说,就是很有“老上海”的感觉。在2006年创业之前,张开宇也是在时尚精品行业打工。之所以自己开店,张开宇说是为了自由,“开了店以后,基本上每天就睡到自然醒,爱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并且每年都有三四个月时间到外面去旅行,那就非常自由。”
凭借对行业的敏锐嗅觉和日积月累,张开宇的店在十年后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就是在15、16到17年那几年,销售额一年能到500万左右,毛利率大概是在40%。”但到了2018年,张开宇的店就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客户群发生了变换,“以前有20%是住在上海的外企高管,就是外国人,但18年以后,这些人几乎都消失了。那时候我们都感觉很奇怪。”
他同时发现周围做生意的朋友也都出现了问题,“好几个朋友就在那两三年时间,居然都一一生意失败、破产了,还有一个人跑出去躲债了;其中一个曾经做得挺成功的,在全国有近一百家连锁店,也在那几年就失败了。”

舒坦的日子
在成都的莫先生也是在2018年开始感觉到自己店里的顾客群消费下降了。
和张开宇一样,莫先生曾经也是上班族。2014年,因为偶然的原因,莫先生跨足到他并不熟悉的餐饮行业,在成都龙泉驿一所大学旁开了一家自助餐厅,卖70元一位的自助餐,“就是烤肉、小火锅,日餐、西餐等等,种类比较多,价格又比较便宜,主要针对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这家餐厅定位非常成功,一路顺风顺水,做到2016年顶峰时期,一个月的销售额能达到60万。莫先生很快又开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莫先生说,那一阵的日子过得很舒坦,“基本上不会愁赚不到钱,没利润等等,基本上每个店都在盈利,你不需要到处补窟窿。那个时候想法就活跃起来了,想去做个品牌,把品牌打出去,类似这样的东西。”
但到了2018年,店里的生意就开始下滑了。莫先生首先从大学生们的消费上发现了变化,“店就开在大学旁边,你明显地感觉到大学生的零花钱少了。有时候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家里给的零花钱在减少,不断在减少,所以他们就必须降低自己的消费,而且你出来吃顿饭本来也不是刚需啊。”
走到分水岭
但对于2018年生意这种变化的原因,张开宇和莫先生都有点后知后觉。
“18年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因为生意这个东西有好就有坏,传统行业嘛,有涨就有跌,但到了2019年是持续的不好,我也和一些同行去聊过天,所有人的反馈都是这么一个情况,”莫先生是回过头去看,才发现主要是经济大环境的问题。
“总是觉得哪里出了问题,但看新闻联播,看中国的官方媒体,就觉得所有都是好的,”张开宇开始学习研究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他找到的答案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后来明白是房地产绑架了经济,老百姓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买房,所以就导致内需不停地衰退。”
在很多方面,2018年并不像是败相初现的年份。这一年中国政局平稳,习近平刚刚开启作为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第二届任期;新就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位是新人,包括栗战书、汪洋和王沪宁等等,但外界并不认为他们以后会具备替代习近平的潜力。
而2018年的中国经济相比于2010年代的其他年份并非特别差。关于中国经济出现拐点的说法早在2012年就出现了。在2018年,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预定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6.6%的目标,似乎是差强人意。
但或许因为2018年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对这一年的经济表现尤其敏感,媒体纷纷指出,6.6%的增速是中国1991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分开季度看,经济增长率更是逐渐降低的,一季度同比增长6.8%,然后依次是6.7%,6.5%,和6.4%。
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信号,但他们对此的解释莫衷一是。有人归结于这一年开打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格局。曾在1990年代初预言过中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奥弗霍尔特博士(William Overholt)在2018年出版新书《中国成功的危机》(China's Crisis of Success),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分水岭,除非转化成更为市场化的经济体,才能保持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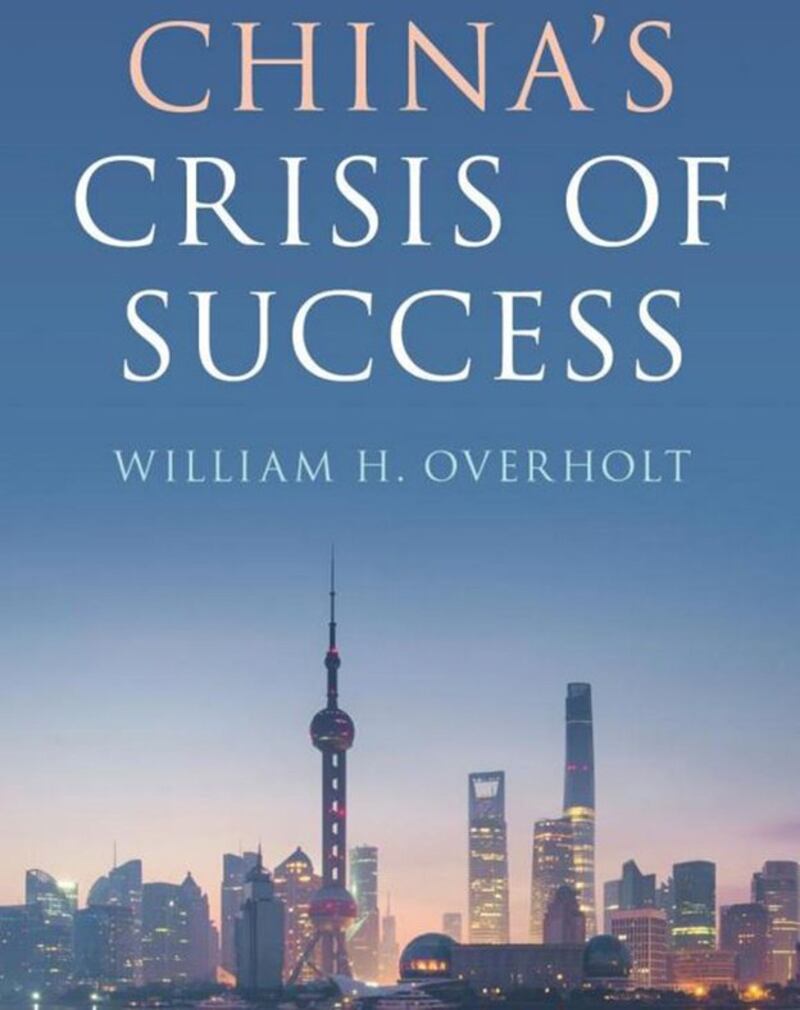
避之唯恐不及
宏观经济下行的雷声虽然还没有逼到眼前,但张开宇和莫先生,一个在长江尾的上海,一个在长江头的成都,不约而同开始收缩生意的规模。
张开宇在2018年就退租了一半的店面,“一个月把各种成本算下来,包括租金、员工,还有压货的成本、管理的成本,估计一个月能省个三四万。”
莫先生则开始关店,“是陆续关的,因为不止一家,就是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最后关闭的那家是2022年5月。”
经济形势虽然不好,但两位老板感觉自己所处的营商环境还过得去。虽然政府主管部门不时会对他们的经营有干扰,但他们总体感觉,无论上海,还是成都,在中国都算得上对民营企业比较友好的城市。
莫先生说,他做了几年的餐馆,虽然也遇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刁难,但基本上都能躲过去,“反正中国就这样呗,和他们打交道,说难听点就是耍赖,说好听点,就是要灵活走位,不要被他们粘到。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还好吧,也没有太为难你。”
他说的“没有太为难”有好几次:其中一次,餐馆因为消防设施没过关被开罚单60万,但实际并没有被征缴罚款;“包括环保也是,这不行那不行,天天约谈你,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吓唬吓唬你,没有非要你怎么样,可能会找点麻烦,但实际上没有。”
但同时,莫先生也从成都市政府的政策中得到过好处。莫先生的自助餐厅因为在2018年成都美食节上赢得一个奖项,在贷款方面得到了优待,获得了扩张品牌的一笔贷款。
同一时间在上海的张开宇则会为店里不时受到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而烦恼,“他的干预会很多,比如要求你的招牌要统一,店面方面的设计要按照他的审美来做,但你知道他们的审美是很糟糕的,本来是很好看的一个店面,会被他们弄得非常难看。”
陈开宇有些叹息地说,自己的底线比较低,“中国人基本上都已经逆来顺受习惯了,对这种事情,我们都觉得,只要它不来管你,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张开宇和莫先生对政府都是避之唯恐不及,而杭州的葛平从2018年创业开始,他的业务就和政府有紧密的联系。
保的都是头部企业
葛平创业之前在企业里为人打工,做管理咨询,创业后也主要是在这个领域从企业和政府拿咨询类的合同业务。他为政府所做的业务中还包括维稳机制的咨询,即防止社会恶性事件的政府反应机制咨询。
葛平很清楚政府业务的门道,“特别是做政府咨询这一块,其实说到底还是权力寻租,这个业务他之所以给你,可能是因为你认识某个官员,他对你的专业性有客观的评价,然后你也可以私下里给他一点好处,做一点利益交换。”他强调,这一块业务政府表面上也有招投标,但所有这样的招标都是内定的。
凭着人脉和对行业风向的准确把握,葛平的公司很快在2019年就达到了行业的一个高度,“最好的时候,一年签的合同大约有四十万,就是指纯收入。我们是属于小微企业,在这一块能达到区域内的前十。”
但无论是葛平这种与政府利益存在一定捆绑的咨询企业,还是莫先生的餐饮企业,或张开宇的时尚精品店,在正常时期要战战兢兢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而在面临疫情来袭和政府一刀切的封控政策下,又都难以从政府获得必要的帮助。
葛平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企业在疫情期间从杭州政府得到的救助太少,“我这个企业得到的唯一一个政策是在(疫情)爆发之后,有连续十个月时间,政府有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疫情期间,葛平的咨询公司合同数减少了;因为地方政府缺钱,公司过去的一些政府合同也无法续签。由于做咨询的缘故,葛平对市场上不同企业的心态比较了解,“对于我们这种小微企业来说,从市场端看,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从多数企业的情况来看,疫情这三年,(政府方面)也没有和我们企业主有任何沟通。”
政府的救助似乎离葛平们很远,但离其他一些企业则比较近。在中国国务院2022年6月初发布的《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中可以看到,在融资、复工复产政策等方面,中央政府支持的都主要是重点企业。
《措施》中也提到,抓紧办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留抵退税并加大帮扶力度。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今年初报道,2022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1.7万亿元,占全年减税降费总额的比重约四成。但这些政策下去,三位在不同城市的小企业主都没有感受到实际的优惠。
葛平则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我个人的感知就是,最近一两年政府也不装了,他保的还就是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上市公司,还不算新三板的公司,就是A股上市公司,政府就是根据这个层级来的。”
伤筋动骨
实际上不同地方政府都有过一些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莫先生所在的成都在疫情前就有困难企业稳岗补贴的政策,莫先生旗下一家餐馆的员工每个都曾得到一个月百元左右的补贴。这种政策在疫情三年期间都有延续。
但这些修修补补的政策似乎都难以挽救疫情封控让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的困局。
莫先生回想疫情这三年的日子,早已不复2016年巅峰时期的舒坦之意,“我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估摸着这一关肯定是有点难过了,也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给家里也交底了,就说这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行就行,不行就准备宣布撤了,不能再做这一行了。”
即使是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莫先生依旧觉得压力无时不在,“因为每天你还要付工资,有那么多员工,他们还是要吃饭的,对吧?”而且莫先生的房租即使在疫情期间还是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
莫先生目前已经身在美国加州,他对中美两国的疫情措施有很清晰的对比,“就是太久了,我当时以为封三个月就差不多放开了,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三年下来,让人伤筋动骨了。反正我圈子里不少人就是倒在这个地方,就是致命一击,这一击就是敲脑门儿!”
店主眼里的社会面
在让人惶恐不安的疫情封控下,莫先生看到的不仅是身边生意人的倒掉,还有整个社会氛围的裂变,“之前那些骑手都是大叔大妈之类的,后来就有很年轻漂亮的小女孩来送外卖了,而且一聊,好多都是高学历的开始来送外卖,就是说整个就业状况不是很好啊。”
从外卖骑手的身上,莫先生直接体会到中国社会真实的情绪,“我感觉到他们身上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本来赚得又少,又没有其他的活路,脾气就很暴躁;单子又少,来得又快,就催啊,经常和我的员工吵架闹矛盾。”莫先生不得不经常安抚他的员工,让他们一定一定要忍住,不要和外卖员对着干。

莫先生说他看到的这种情况在2021-2022年尤其严重。实际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经济的起伏,中国社会的就业情况经历了大起大落。2021年不少地方复工复产,失业率一度回落,但从当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失业率再度走高。仅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而言,在莫先生关闭最后一家餐馆前夕的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尤其青年群体(16-24岁)调查失业率高达18.2%(2023年4月,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0.4%)。
面对逼仄的经济空间和日趋恶化的社会形势,手里有点积蓄的民营企业家似乎有更多的路可走。张开宇从自己身边接触的富人阶层观察到,“整个社会最有活力、最有钱的那些人,我说的是通过正当经营做得非常成功的人,这些人其实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这些人是最有能力离开的,而且是最有意识离开的,这些人我觉得正在离开,或者是已经离开。”
但在他看来,这只是极少部分人的选择,“对于大部分普通的店主,或者说中小企业家,他们其实是离开不了的,只能在这里挣扎,挣扎着生存。”
张开宇和自己的猫于2023年3月迁居到了美国加州,虽然当时中国已经结束了清零政策,但他依然充满了失望,“他解除这个政策也并不是因为他从全世界学到了什么教训”,他仿佛很高兴自己说透了这个秘密,讪笑了两声,又说到,“他只是因为没钱了坚持不下去,或者是老百姓反抗太厉害了;他根本不是出于一种理性,关注到老百姓的健康,或者是基本权利生存权等等。”
葛平在杭州看到的社会面就是老百姓的反抗。2022年11月27日晚,白纸运动在全国铺展得最广泛的那个晚上,葛平跑去了杭州白纸运动的现场,靠近西湖的苹果电脑店前,“到后面,那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女生,完全是一种‘冲塔’的姿态,八点钟之前,他们(警方)所有的包围圈都已经布置好了,包括他们的领导就按照这个时间,还有一辆车,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但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去冲塔。”
在这场中国多年未见的社会运动中,葛平看到了社会的希望,同时他从维稳体制的角度有一个新的发现:各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个事件时也在躺平,“为什么白纸革命在几十个城市发生,其实在这个当中,在维稳机制当中,当时他们是存在懈怠的,包括后台的网安数据我们也看得到。”他认为,这也体现了某种社会的进步。

“倒查11年”
白纸运动席卷全国后,中国政府迅速在去年底结束了疫情封控政策,到今天已经半年有余。中国社会似乎正慢慢走向正轨,疗愈疫情封控三年造成的伤害。
来自成都、上海和杭州这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城市的三位小企业主都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安排。莫先生说,他跑到美国就是来躲债的,他已经不愿谈对餐饮业未来的展望,“说实话至于什么时候能恢复,我根本就不想关心这个事。因为我已经不在这个行业做了,其次我人也不在国内,关心也是瞎关心。”
张开宇则有些担忧,他的母亲前不久在国内中风,躺在重症监护室不能说话,但他的妹妹告诫他不要回去。葛平说会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暂时接不到业务;自己的公司还有六名员工,虽然亏着钱,也要给他们发工资。
国内民营企业的信心普遍没有恢复。中国政府似乎也明白民营企业这种处境。近几个月以来,各地政府接连召开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就在7月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与三一集团、农夫山泉等5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会谈,想听取民营企业的真实情况和相关政策建议。
但小业主们看的却是实际发生在民营企业身上的事情。“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个环境已经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张开宇这样感叹说。
2020年底蚂蚁金服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叫停,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这一轮打压民营企业的标志。而就在今年7月7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71亿元人民币。
今年二季度,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对当地的陶乡餐饮有限公司2012年至2015年的偷税行为追罚1425万元。网友以“倒查11年”的标题在网上传播这一消息,充满了警示的意味。
这些做法看似有法律和政策的依据,但张开宇说,他对政府种种的举动看不到边界,“关键是他可以任意地运用他的权力,想让你生就生,想让你死就死,没有任何法律的界限。”
与政府经常打交道的葛平则认为,对中小民企来说,经营环境很难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现在是政府给头部企业站台,但站台之后,这些头部企业能不能生存?比如这些房地产企业,他们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头部企业都不好的话,那你指望中小微企业变好,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葛平还在高校为大学生做创业辅导,但他对目前的创业环境持否定态度,“目前的市场环境,我要给一个建议,就是风险太高了,政策支持太少了,就如在疫情期间,那你对创业者有什么支持呢?没有任何支持,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我们的活法与我们的期待
但在经历了白纸运动后,葛平却对中国社会自身的力量有一种别样的乐观,“目前来讲,民智已开,只是要更多地去认识历史,特别是要认识中共的国家机器是怎么运作的。”
他暗示地说,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要认清自己所在的阶层和对生活的期待,“官二代或富二代有他们的活法,但我们普通人,无论是做技术的,还是打工的,或者是做商人也好,我们要有我们的活法,我们要有我们的期待!”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