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后,对知识界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压和钳制,造成知识界普遍的犬儒态度。同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转而拥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威权政府大唱赞歌。但即使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下,仍有知识分子个体在为尊严和承认而坚持抗争。以下是本台【习近平这十年】系列专题报道的第六集,
【#习近平这十年】之六:知识分子的“为奴”和斗争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October 18, 2022
习近平上台后,对知识界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压和钳制,造成知识界普遍的犬儒态度。同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转而为 #威权政府 大唱赞歌。但即使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下,仍有 #知识分子 个体在为尊严和承认而坚持抗争。 pic.twitter.com/OluW4u5HFG
这几年,吴强时常要拼尽全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2020年10月,吴强和妻子从德国度假回国,在上海浦东机场被当地管理机构以疫情防控为由把他和妻子分开隔离,这引起了他的激烈反抗,“这实际上是对我个人尊严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就绝食,抗议这种在疫情期间无法保持基本尊严的伤害。”
在吴强绝食35个小时后,管理机构才被迫接受吴强和妻子在一起隔离的要求。
知识分子的尊严
但吴强对尊严的抗争更多时候是失败的。今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作为清华大学前讲师的吴强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维持了清华大学去年对他做出的解聘决定。
这个判决距离2015年清华校方因为吴强从事香港“占中运动”等社会运动研究而将其停职已经7年有余。吴强当时已经明白,这类研究的大门正在关闭,“比如当时的太石村事件,后来的乌坎事件等类似的公共事件,我自己在做这些国内的集体行动、集体抗议研究,发现这种研究领域本身受到了严格审查。”吴强提到的太石村事件和乌坎事件都是广东乡村因为财务或选举等问题而引发的村民抗争事件。
对法院的判决,吴强并不意外,他迅速在9月21日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了上诉书。吴强对二审同样不报希望,但他说,这事关尊严。

吴强认为,他所争取的是清华大学对待一个有着国家事业编制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也是个体人权的尊重,“尊严就是要靠国家体系来保障、来维护。”
在吴强看来,尊严的本质在于承认,“无论是底层人民,一个胼手胝足的劳作者,还是最高层的领导,或是中间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资本家,得到承认才是尊严的本质,是最重要的。”
承认的政治
但在当前的中国,敢于批评当权者,或者从事引起当权者不悦的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得不到承认的。他们常常被噤声、停职、开除,甚至判刑、坐牢。
就在吴强曾任职的清华园,法学院教授许章润2018年通过网络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把国家引向倒退,很快就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为由带走,并遭到清华大学开除。
类似的案例还有2013年多年批评政府钳制言论自由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被北大解聘,2018年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当地警方强迫失踪,以及今年遭贵州大学开除的经济学教授杨绍政被当地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等等。

敢言的知识分子接连遭到清算,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空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观察到中国知识界在习近平上台后这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在公共知识分子受到攻击后,许多学者不得不做出一种选择:承担专家角色(向政府或市场提供专业知识)或退缩到校园的象牙塔中,最多只能间接参与公共事务。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中国对公共表达的重大限制,发挥公共作用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寒蝉效应也渗透到了专业研究领域。长期从事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在海外也感受到大陆吹过来的凛冽寒风,“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都不敢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较多的联系,就是怕联系会给别人带来麻烦。......2015、2016年好像还可以,2017年以后就不行了,17、18、19就越来越严重。”

郝志东所感觉到的2017年这个分界线,正是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少数族裔民众开始被国际媒体关注并广泛报道的年份。
“革命”之后的流亡
在面临清洗的形势下,有些知识界人士趁着外出访学的机会展开逃亡。
2011年2月底,尚在酝酿中的“茉莉花革命”导致大批民主人士被中国政府抓捕。“茉莉花革命”后,政府开始进一步强化社会管控,同时,较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流亡。
当时在香港访学的原《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长平,被国内朋友告知他有可能被抓捕,便决定暂不回国,目前长居德国。“茉莉花革命”期间被抓捕的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人权律师滕彪2014年也逃亡到了美国。
滕彪告诉本台,“我是2014年9月来到美国,当时是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做访问学者,当时的背景就是许志永、王功权等参与新公民运动的很多人,还包括丁家喜、赵常青等等,都被抓了。”
许志永、丁家喜、滕彪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和丁家喜目前还在中国的狱中。当时在香港的滕彪预估自己如果回大陆,会被再次抓捕。到美国后,滕彪打听到自己的妻子和一个孩子都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没办法出境,“所以在2015年,通过地下渠道,偷渡的方式,我的妻子和孩子才辗转来到美国。”

滕彪2002年底从北大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一方面在高校从事法学的教研工作,一方面也做人权律师,参与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而这十多年中大部分是胡锦涛主政的时期。
“在江、胡时期,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等流亡海外,但与2013年之后相比,人数是非常少的,”滕彪分析说,江、胡时代对于异议知识分子、维权人士等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做一些事情,例如新公民运动、零八宪章联署等等。

“知识分子”的含义
知识分子的流亡在现代史上层出不穷。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大批知识分子出走欧洲;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胡适、张爱玲等一批知识分子脱离大陆,投奔台湾、香港或其他国家和地区。
流亡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判姿态,也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题中之意。“知识分子”的词源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和法国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少数族裔权益的知识分子或文人群体。在其诞生之初,“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的特性包括身份独立,拥有知识,拱卫良知和关怀社会等。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界曾一度流行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曼海姆提到free floating,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漂流的,不依附于某个阶级,不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或党派,这才算是知识分子,”滕彪强调,这些特性方便知识分子对权力保持批判的立场。
他分析说,按照这个标准,今天中国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体制上、经济上的独立,也没有精神上、思想上和知识上的独立。所有的大学、研究机构都是中共控制,他们为了饭碗而不敢独立地发表见解。”
但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可以争议的。魏简教授认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需要判定作为前提的学术传统,“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比如葛兰西,知识分子只是为当权者生产知识的人。在道德主义传统中,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要达到某种道德标准。”他强调,中国并不缺乏愿意为国家或市场生产知识的专家。
若借鉴魏简的这种两分法,在今天的中国,象滕彪、吴强这样道德主义传统下的知识分子显然已大为边缘化,而“为当权者生产知识”的专家则占据着学术职位、社会资源的要津。
国家主义的“投名状”
滕彪在北大法学院的学长、北大法学教授强世功去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负责整个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强世功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论述,作为不成文宪法的形式,中共党章是中国宪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论断被外界概括为“党章即宪法。”

但强世功在学界更为有名的是作为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国的推介人。在二十世纪初叶,施密特一方面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弊端提出了批判,一方面又为德国纳粹党提供理论支持,被称为纳粹的“桂冠法学家”。从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通过刘小枫、强世功等人的著作,施密特的学说在中国学界一度风靡。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同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陈端洪2018年在一份提交给中共决策层的研究报告中,为在香港颁布国安法提供论证,他在其中引用了施密特的理论,并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宪法、法律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对于强世功、陈端洪等人拥抱施密特学说所标志的国家主义,澳门大学荣休教授郝志东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自身可能是相信这种主张的,“这些人也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长大的,......他们的思路基本上是延续原来的思路,因为文革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被追根溯源,阶级斗争的东西从来就没有被彻底否定过。”
但强世功也曾推崇过自由主义。强世功曾在2000年的《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文章《哈耶克使自由成为一门科学》,盛赞哈耶克对自由主义论述做出的贡献。
“2004年,他(强世功)用施密特的理论来分析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在我印象中,那篇文章就是他公开的思想转向的代表,”滕彪分析说,强世功的转向背后有利益的牵扯,这篇谈乌克兰的文章就像是强世功递出的“投名状”,不久之后强世功就进入了香港中联办工作。记者在强世功的北大网页上看到,强世功在2004至2008年期间担任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和法律部调研人员。
强世功没有回复本台记者的采访邮件。
有机知识分子
在国家主义的笼罩下,近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
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台海局势表态说,“我们要进攻台湾像玩儿似的,现在消灭台湾20万军队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是一点代价,道德代价;21世纪了,还打那么多人。我可以告诉你,台军20万人,在我军面前就是一堆肉,是没有意义的。”

郝志东教授分析说,这种论断反映出这些学者真正的认识,“就是拿杀人、死人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们就没有这种概念,......他觉得这种事情就跟捏死一个蚂蚁一样。他就是没有人权的概念。”
对台海问题强硬表态,在中美关系上极力反美等成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标志。包括金灿荣在内,复旦大学的张维为、陈平,《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以及从美国获得社会学博士的李毅等五人因其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在社媒上高调的作风,被舆论借用武林高手的“五绝”讽喻为民族主义的“五绝”。
2021年5月底,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甚至走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最高决策者讲解如何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并提出工作建议。

对于这些以学者身份出场、但与政府立场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人,有舆论称其为“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的论断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启发,在二十世纪初叶提出的。他认为,作为“现代君主”的革命政党是一种历史的力量,知识分子基于与所属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有机联系,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从中国学术网站“知网”的搜索结果可知,过去十多年,几乎每年都有学术文章从肯定的角度反复讨论“有机知识分子”对当下中国的意义。郝志东则分析说,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旗帜下,有机知识分子与当权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他(张维为)去政治局讲课,证明政治局还是蛮器重他的,否则不会请他去讲课啊。换句话说,他肯定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关系到底是谁影响谁?”郝志东坦承,他还在继续观察这种关系,但他强调,关键可能还是当权者,“领导想什么,有个什么主意,就让你来跟我讲,强化我的观念。”
“自甘为奴”
除了权力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立场的可能还包含市场、金钱等因素。司马南、李毅和金灿荣等“爱国大V”们的背后是饶谨担任董事长的四月传媒几十人的团队在社媒上推波助澜,收割流量经济。
吴强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在被驯服后开始转向,“(知识分子)在压力、金钱、市场等诱惑之下,出现一种集体的转向。这种转向需要伴随人对尊严的认识上的变化,伴随人格的变化,需要伴随一种放弃,就是一种自愿为奴的心理。”
除了前述那些游走在学界与舆论市场交界处的“风云人物”之外,学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也在被迫或主动迎合外在的压力或诱惑。
滕彪介绍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就不敢说话,但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不但不敢去批评现有的体制、不公平的现象,而且去加入‘歌德派’,对官方歌功颂德。”
2017年末,中共十九大刚刚将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中国人民大学等至少二十所高校就先后成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底,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才落幕,北京大学就接连成立四个以“习近平思想”为名的研究中心。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犬儒化趋势,滕彪认为,这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它对一个民族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包括精神的独立,都是一种毁灭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从道德主义的传统看,知识分子也正在失去其独立于权力的角色,“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民众的犬儒化,缺少独立人格、缺少批判精神,既是专制极权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极权的重要力量。”
寻求解放的空间
知识分子群体在道德立场上的退缩也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些真空。而这个真空正在被其他人填补。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2019年出版著作《在人民之间》,描绘并分析了1990年代至2015年在中国出现的民间知识分子。这是指的自由作家、民间史家、独立导演、维权律师、记者等不同主体形成的网络。他们反抗政府的压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文化以及身为知识分子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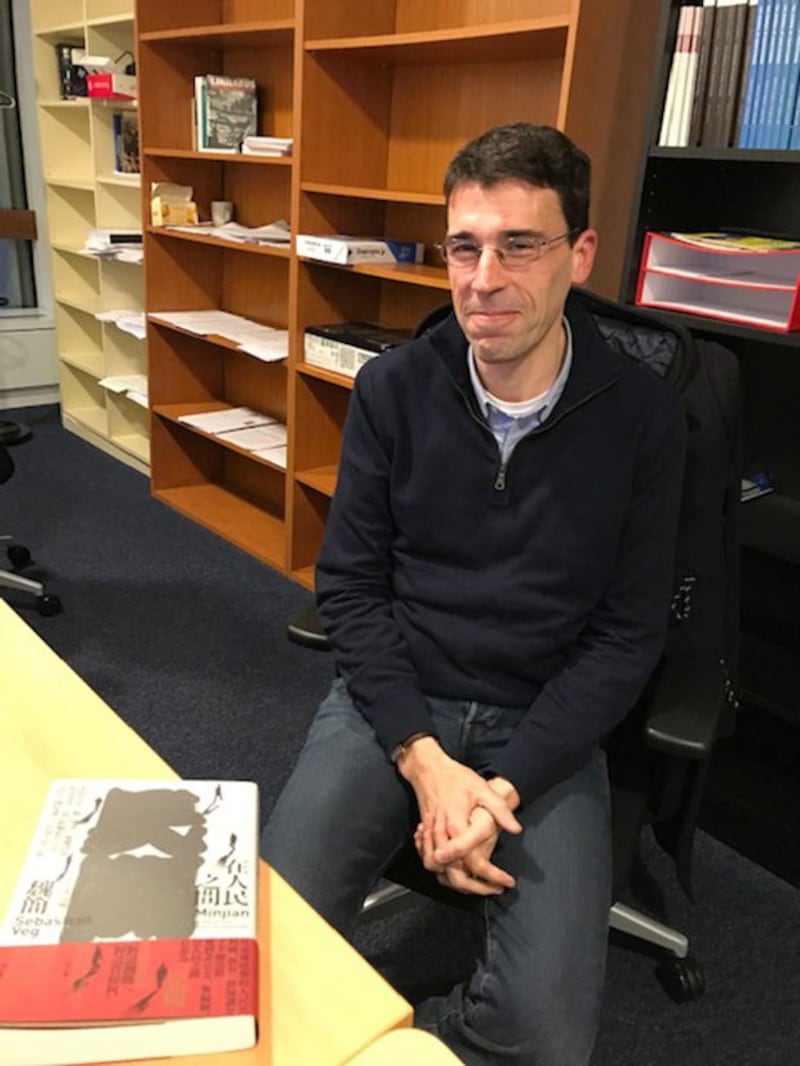
魏简认为,民间知识分子的崛起部分满足了外界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期待,“在中国,自从2004年左右发生了一场关于 ‘公共知识分子’的争论后,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就受到了国家和公众的批评。他们被指责,只有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或为商业甚至外国利益说话。民间知识分子的出现或重新出现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将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具体经验重新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
身在北京的吴强则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坚持知识分子的职守。在被中国现存的学术体制排除后,吴强已经很难在国内发表学术作品。但他却感觉自己意外地获得了某种“解放”,“我在国际媒体上更多地发表了评论,我在个人专著的研究和撰写方面接受了各种独立机构的邀请和资助,......一定程度上我是从这种严格的审查中摆脱了出来。”
吴强认为这种解放并不是偶发的,“这种解放并不是只会发生在我个人身上,而是凭借勇气、能力和专业性可以达到的,还有国际社会和国内残存的公民社会的重视和支持,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吴强强调,在中国威权体制残存的言论空间中,他所坚持的政治学观察和评论成为了社会稀缺的反馈,艰难赢得了当权者的承认。他说,为承认而斗争正是现代性的核心。
(记者:王允 编辑:安克 网编: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