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专栏上星期五播出和刊登的《王沪宁“文革反思”的与时俱进》中,已经介绍过了二十五年前《江泽民的幕僚》书中的王沪宁专章,《专家当智囊,教授变幕僚 --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王沪宁》首段内容。出版此书之前,笔者是第一个向外部世界介绍王沪宁的媒体人。
该书中介绍说:一九九五年初,如果说江泽民借反腐败为名,成功地整垮了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狠狠地教训了以邓家后代为代表的一批经商“太子党”的举措,一度起到了令党内党外刮目相看作用的话,他将上海复旦大学青年教授、著名政治学家王沪宁正式纳入自己门下,则在大陆知识界阶层引起一番强烈回应。此消息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初,即传遍上海、北京两地。王沪宁接旨进京前,向朋友透露的新任职务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长。政治组长仅仅是个正局级职务,但室务委员则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
日后,直到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官方宣布的王沪宁进京“下(中南)海”时间的次年,记得当时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已经被销售到第十版,笔者从王沪宁的一位博士生口中得知,他王沪宁进京效命江泽民的最早时间是1994年夏天。日后笔者仔细研读了王沪宁于1995年一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王沪宁个人日记),从具体内容中找到了他1994年整个夏天都在北京北戴河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佐证。
也就是说,如果说以首次参与起草中央全会的重要决策文献的时间算起,政治学学者出身的王沪宁踏入中南海,成为中共最高决策层之重要幕僚,已经长达二十六年时间了。
奉诏进入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七月,当时的王沪宁未满四十岁,如今的王沪宁到下个月,即二零二零年十月即年满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共政权正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
而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奉诏进入中南海参与起草江泽民的“独立宣言” 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之前,事实上他王沪宁已经在“体制外”以“知名青年学者”和和复旦大学教授身份,积极进行“理论介入”很长段时间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完成硕士学业之后,王沪宁至少是上海方面的同批青年学子中,进入角色最快者之一。用其崇拜者的话说: “出道甚早, 八十年代曾经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独领风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王沪宁的论文和译作在《社会科学战线》、《国外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刊物一篇接着一篇,令同行新老学者不得不瞪大眼睛关注;其触及当时最被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时论文章则在《读书》、《世界经济导报》等理论先驱报刊,及《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拥有众多知识分子读者的报刊上连篇累牍,不但将影响力扩大至政治学专业之外的学界领域,也逐渐受到当时的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上海市领导人的注意。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观》、《初级阶段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长短立论,曾引发起出许多或赞成或反对的讨论意见。其《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功能的国际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体性》、《论政治透明度》等文章,仅从标题看便给人思想非常“前卫”的感觉;而《当代美国民主共和制比较研究》、《当代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当代政治学分析》、《国家主权》等文章和专著,更给人以研究视野十分开阔的印象。
王沪宁自己解释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是:“我的长项是政治哲学,对此道一向念兹在兹。但在中国变革的大氛围中,终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热烈运动之感召,动手写起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鬼使神差竟然写了一些,而且兴味愈增……,“颇有点(理论)‘介入’的味道。”
这里的“介入”二字的引号是王沪宁自己使用的。
这段时间里,其崇拜者对王沪宁“独领风骚”四个字,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理论界认同者有多少,令人怀疑。不过如此肯定王沪宁的人同时也承认,“文人相轻”。理论界本来就是谁看谁都不顺眼。
确实,王沪宁出道之始,即不断遭受各种批评。比如认为他的著述过于“浅白”,不够“理论化”,并不具备“程式化”特点,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毛主义卫道士认为,他的观念和理论是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支持改革政策的党内理论工作者认为,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义解释新问题,其见解和主张起到了赋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现代实用意义的积极作用;而从理论基础上否定中共建党治国之指导思想者则认为,他不过是学会了一些《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没有的政治学时髦术语,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图解马克思主义“新意”,充起量具备一点为中共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找出“现代理论根据”的实用价值。更有看不起王沪宁的人干脆认为,他的所谓“政治新论”不过是把马列文论、邓小平文选及西方的《君王论》、东方的《资治通鉴》“一锅烩”。

无论哪种评价较为中肯,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沪宁即开始在大陆思想理论界显露头角,一度曾是上海复旦大学最年轻的人文学科副教授,在整个大陆的政治理论界是叫得响的几位青年学者之一。
大概从一九八八年开始,王沪宁“理论介入”的冲动渐渐淡了下来。对于外界褒贬参半的评价,王沪宁统统回报以不经意的微笑,借编辑自己作品集之机诠释自我说:“我一直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生活:清心寡欲地做学问,不受外部纷繁世界的骚扰和诱惑,象鲁迅先生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相信,学问出于清静,应当保持‘大脑卫生’……。
有评价王沪宁的人士说,他“曾经是一名教授,教书育人是其本分。但他爱这份职业,并视其为乐趣。”
而他本人在《收录于政治的人生》一书的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记中说:作为一名教师,给学生上课是一种快乐。学生能给他一种生命的交响,一种活的知识对象,一种流动的意识过程,一种双向的信息交流。这大概是任何其他职业均不能实现的。这是老师的最大乐趣。他还认为什么乐趣也不能比塑造生命的乐趣,尤其是塑造生命成功的乐趣更乐趣。
但写下这段文字后不出半个月,他就自己把自己安全“异化”了。
王沪宁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奉诏进京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即被安排住进中央警卫局招待所,等待江泽民的亲自召见。
这个当时的中央警卫局招待所隶属于中央警卫局服务处。日后外界有报道说,王沪宁的第三任妻子原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处服务员,与王2014年5月结婚。如果这则消息属实,那么他王沪宁与出身中央警卫局服务员的第三任妻子结婚的时间,已经是他第一次住进中央警卫局服务处招待所的二十年之后了。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引述了王沪宁首次奉中南海之诏进京之后,曾赋《夜游长安街》一诗抒怀:清雨忽降净京城,枝绿墙红照夜灯。信步轻盈伏串露,合手重凝振拱门。
指观世事出清淡,笑看人生入深沉。过客匆匆独寂寥,方识厚意又得闻。
这其中“指观世事出清淡”,显然是他过去一度为自己设计的那种生活:“清心寡欲地作学问,不受外部纷繁世界的骚扰和诱惑,象鲁迅先生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当时他的自以为“学问出于清静,应当保持‘大脑卫生’……”。
接下来的一句“笑看人生入深沉”的“笑”字,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深沉”二字,无疑说的是自己从此踏入的中南海的“宦海”。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汉语“下海“二字的字面意思之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始就引申了许多经济和政治色彩,一般指放弃或保留原来的工作去经营商业和创业。
而当年的王沪宁则是把从复旦大学步入中南海勤政殿的转换人生“跑道”的行为,用“下海”二字形容。这是当年王沪宁的一位门生向笔者复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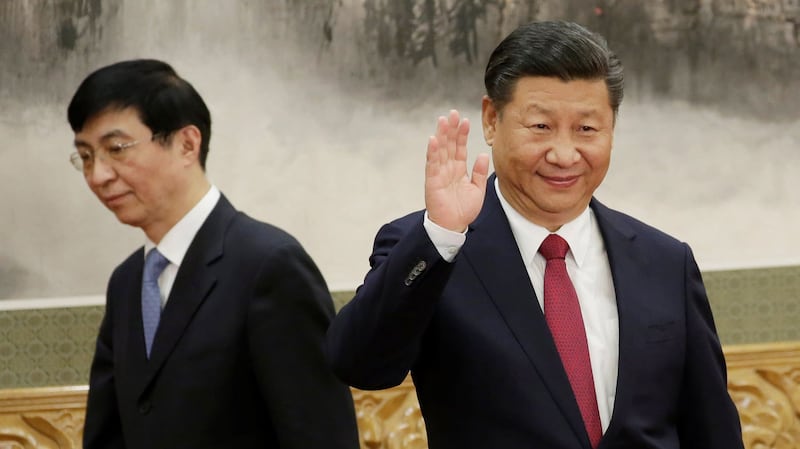
众所周知,当年的中国大陆人辞去公职“下海经商”曾是一种“冒险”行为,是谓丢掉“铁饭碗”,捧起“泥饭碗”。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王沪宁为什么也用“下海”二字形容自己也是把复旦大学教授的“铁饭碗”换成了中南海里的“泥饭碗”,其诗中的“深沉”二字应该是隐喻了王沪宁对日后在中南海里的“宦海生涯”莫测高深的不确定感。
在民间评论王沪宁的文章介绍说:王沪宁涉猎极广,阅读量惊人,几乎无书不读,无时不用功。他在《政治的人生》一书的自序中说:“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法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白天,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没有工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时候,大多也用于作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专业的厉害。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去思考。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自己在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一个人多年坚持这样的习惯,每日回顾过去的一天,在读书中思考和感悟,或总结、或自省,并将此作为思想享受。
王沪宁进入中南海之前确实读书甚多,涉猎面甚广,这从王沪宁自己对外公开介绍过的他的日记内容中可以看出。这可以也是为什么,他给习近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能够开列出那么长的一串书单。
一九九四年七至十月在北京和北戴河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期间,王沪宁仍然坚持每日夜读,偶有星期天被起草小组准假的机会,便在白天时间狂书店,“淘”书摊。
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被公开对外发表后,人已经从北京回到上海复旦大学家中的王沪宁在日记里记述了如下一段内容:凌晨读《毛泽东的秘书们》,写了毛泽东的六大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江青、高智和罗禄光,有丰富的材料和细节的描写,对过去的很多事情有了新的了解。披露毛泽东对诗的一段评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是写诗人的深刻体会。
在此之前,虽然他王沪宁参与了十四届四中全会之重要《决定》的起草,但是从对外名份和“组织编制”的角度,这段时间仍然还可对外以“体制外学者”自诩。
但完成这份阶段性工作回到上海之后,他显然在是否接受江泽民等人的要求、“下海”充当中共最高决策层职业幕僚的问题上,还“思想纠结”过一小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段时间里特别研读《毛泽东的秘书们》,似乎是竭力要从中晤出“不足为外人道”的中南海里面的人们的“冷暖自知”。
王沪宁曾经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常有,而政治学不常有’。自己过去在写政论文章时,完全是受变革时代的召唤,逐渐地悟出了责任、良心和向往……。”
“纠结“之后,他最终放弃了“不常有”的政治学,“下”到中南海里终生效命于“常有”的中国政治 -- 严格地说,是中国共产党之政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